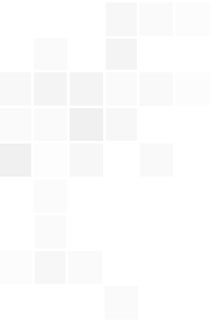近年来,由于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大量土地需求,征地拆迁类纠纷事件频发,尤其是涉及农民利益的集体用地补偿方式。而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土地供需矛盾日益扩大,各地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土地是农民的命脉,如何让改革释放最大的“土地红利”,又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失,十八届三中全会或将进一步明确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有不少内容,包括继续进行农地的确权、登记工作;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方式的多样化;通过信托、抵押等方式与金融创新相结合;通过转包、出租等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益等。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理顺了中国目前的土地问题,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将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成为稀缺要素,社会各界对土地改革颇为瞩目,因此,土地改革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土地改革该走向何方?社会各界对此讨论颇多。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宅基地闲置的问题也随之凸显。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宅基地有近10%~20%处于闲置状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383”方案中关于宅基地有抵押和转让权的部分,让不少在外打工的人格外关注。近日国土部发布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农村闲置宅基地实行自愿有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有稳定的其他居住条件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申请,采取置换、奖励、补助或者城镇购房补贴等方式协商收回空闲或者多余的宅基地。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该模式典型案例是广东南海、北京郑各庄。另一模式是通过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方式,将原有的宅基地复垦成土地,多出来的用地指标,部分建房安置农民,部分通过出让或允许村集体自主开发来实现土地收益,这一模式在成都灾后重建的部分地区得到体现。
但是,笔者认为农地流转应该审慎,主要原因:一是,中央关于流转的两条规定——“自愿有偿依法”和“用途管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规避,一些企业通过流转取得农地之后,往往改变了农地用途,进行商业开发,而一些土地的流转过程也不合规范,往往是企业跟村集体合谋完成,并未征求农民的意见;二是,宅基地流转机制缺失,没有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机制,不但存在大量的隐性流转,也导致大量空心村出现。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但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从最开始三来一补加工企业落地,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都存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隐性市场。在这个隐性市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流转是踩着国家法律“红线”进行,包括各地屡禁不止的“小产权”房。三是,尽管土地流转政策被各方给予高度期待,但对于很多生于农村的人来说,土地还有一层“根”的意义。很多人认为:“现在人上年纪了,还是想家啊。回去家里也没人了,孩子老婆都在外面,但还是要回去。叶落归根嘛。”
所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经验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确权、监管、收益和小产权房。若要改革继续深入,规范运作,还需要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摘自:http://www.he.xinhuanet.com/zfwq/dingxing/wangping/2013-11/19/c_118206299.htm